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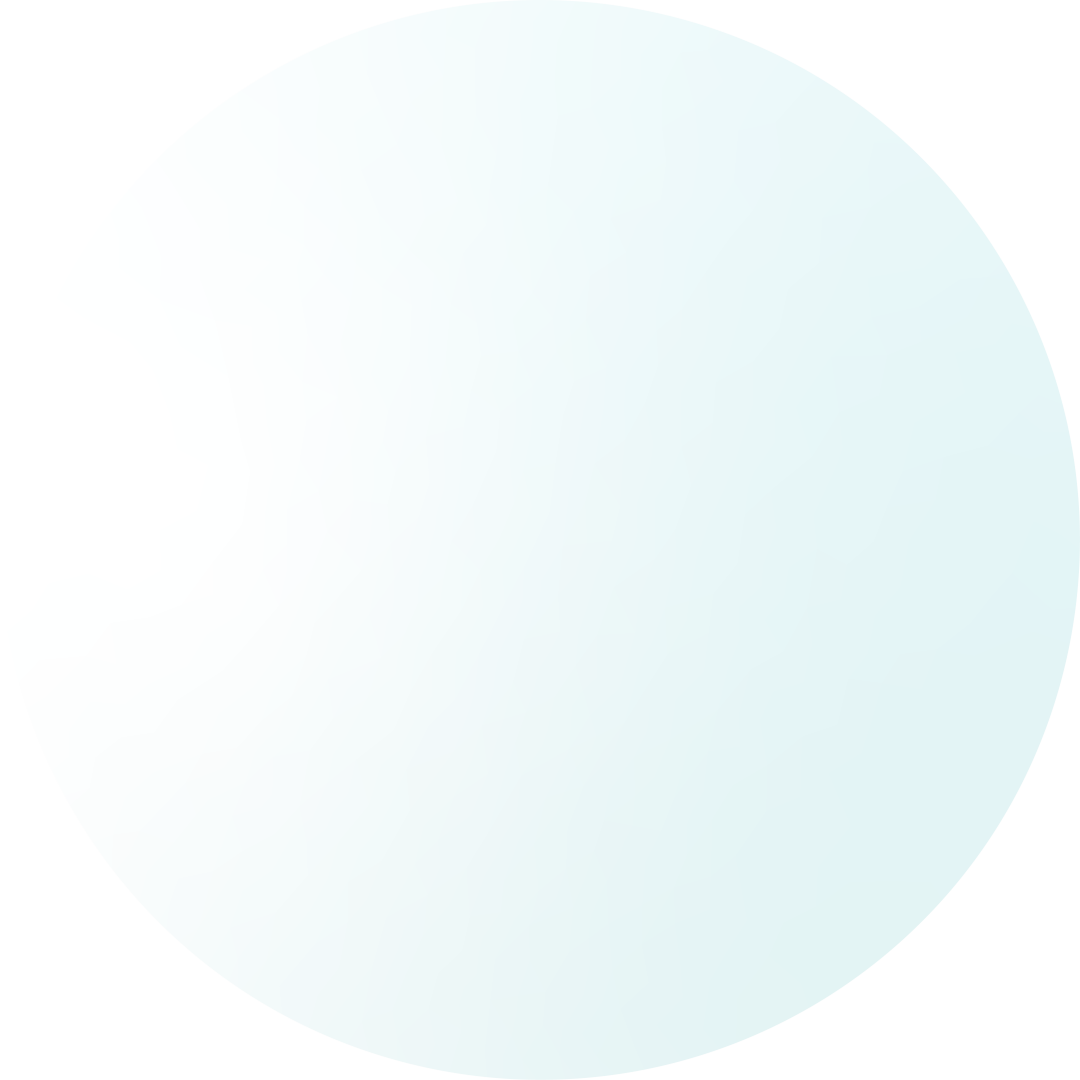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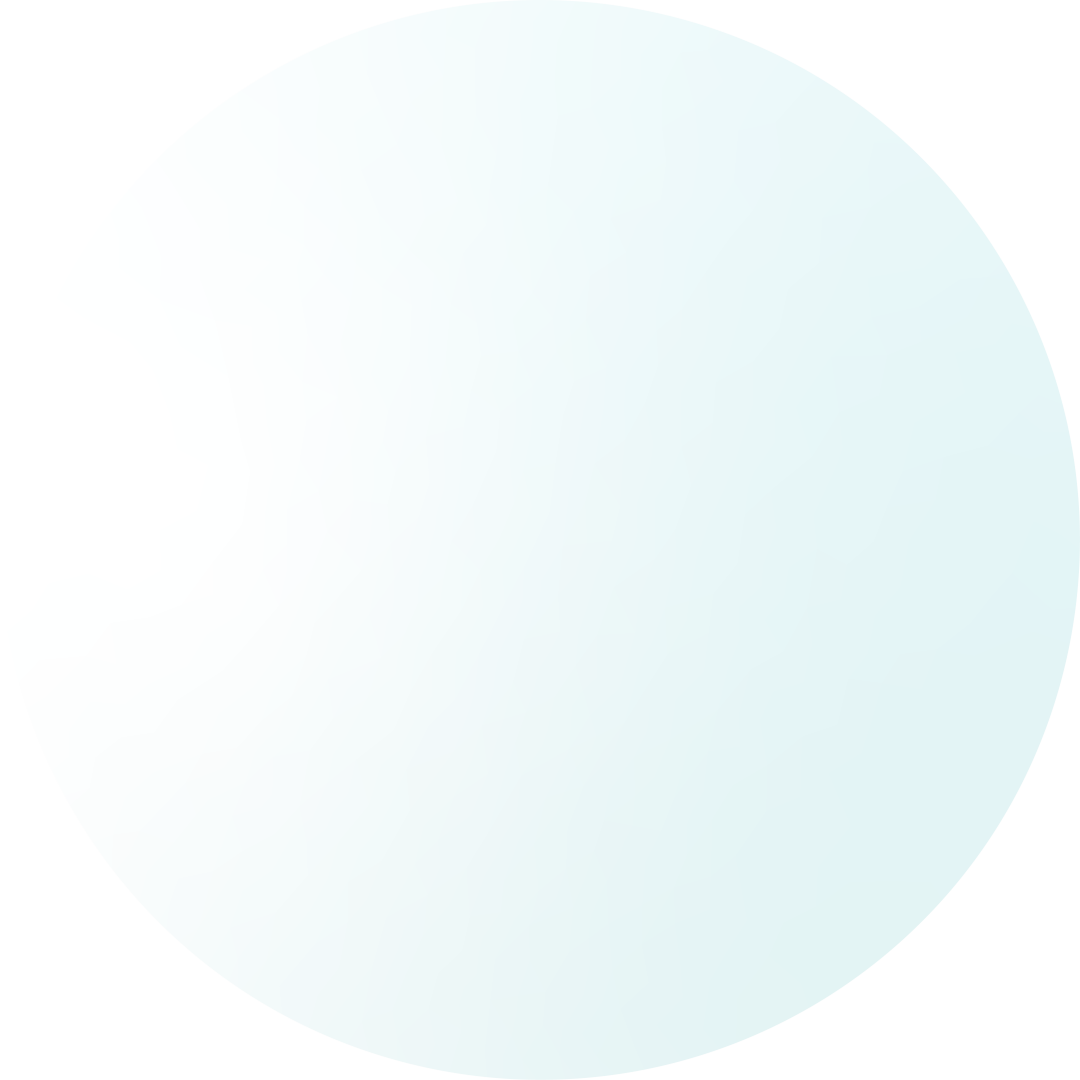
袭警罪自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以来,相关案件数量明显增多,但由于法条文义的抽象和新司法解释的缺位,刑法理论和实务中对于该罪名的理解和适用存在较大分歧,其中之一便是基于该罪名保护法益的特殊性,行为人向民警赔偿或道歉后取得谅解的法律性质及后果。近日,《刑事审判参考》第139辑刊载的1589号林某袭警案,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不能将受害民警个人对犯罪分子的谅解作为对袭警犯罪必然从宽处罚依据”的裁判观点。对此,笔者虽然赞同文章从袭警罪保护法益角度分析论证的逻辑,但认为上述要旨过分强调袭警犯罪对秩序法益的破坏,忽视了民警个人人身安全法益的地位,且与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的办案经验及普通民众对法律的朴素认知存在距离。为此,笔者结合当前对袭警罪的研究成果和具体案例,发表几点浅见,与各位同仁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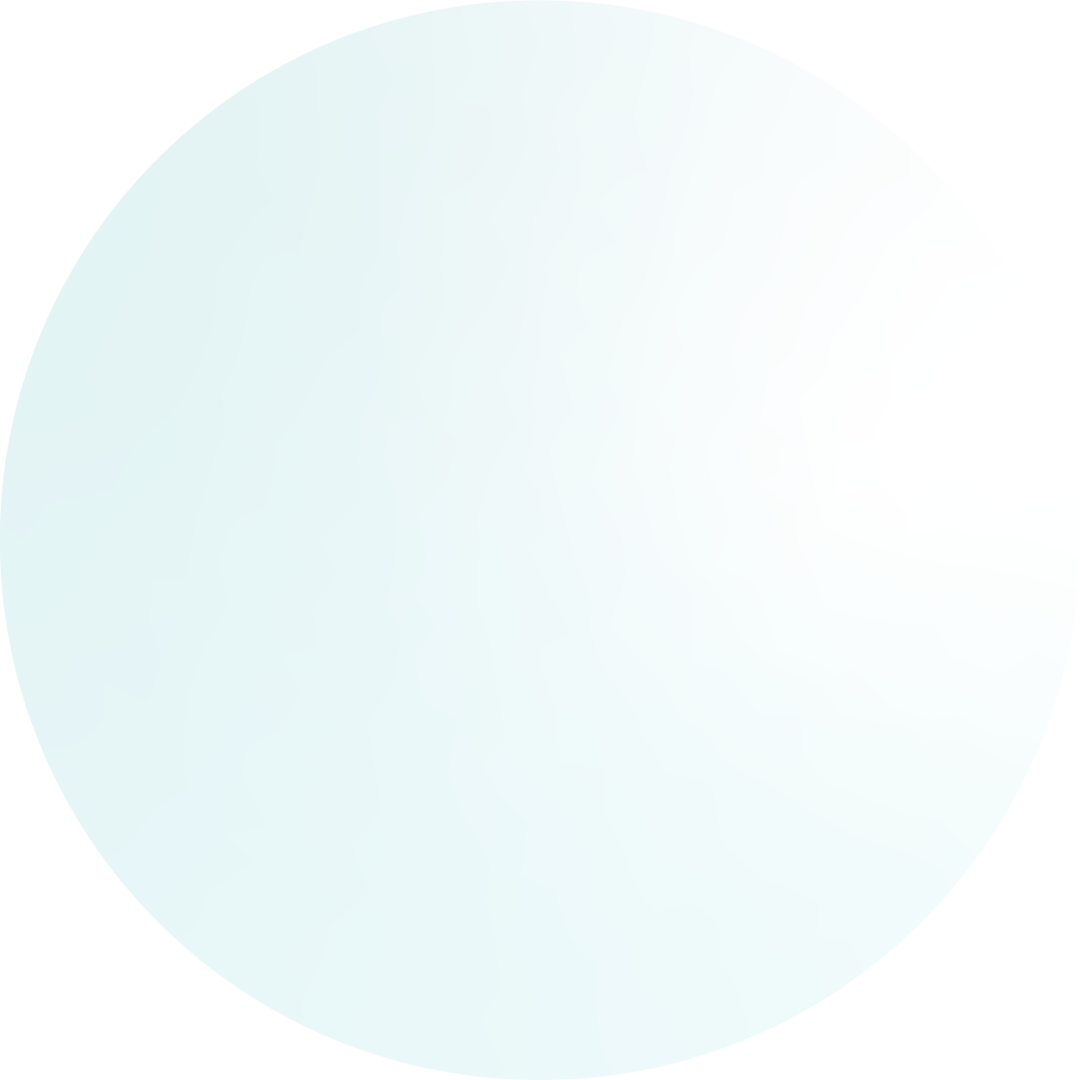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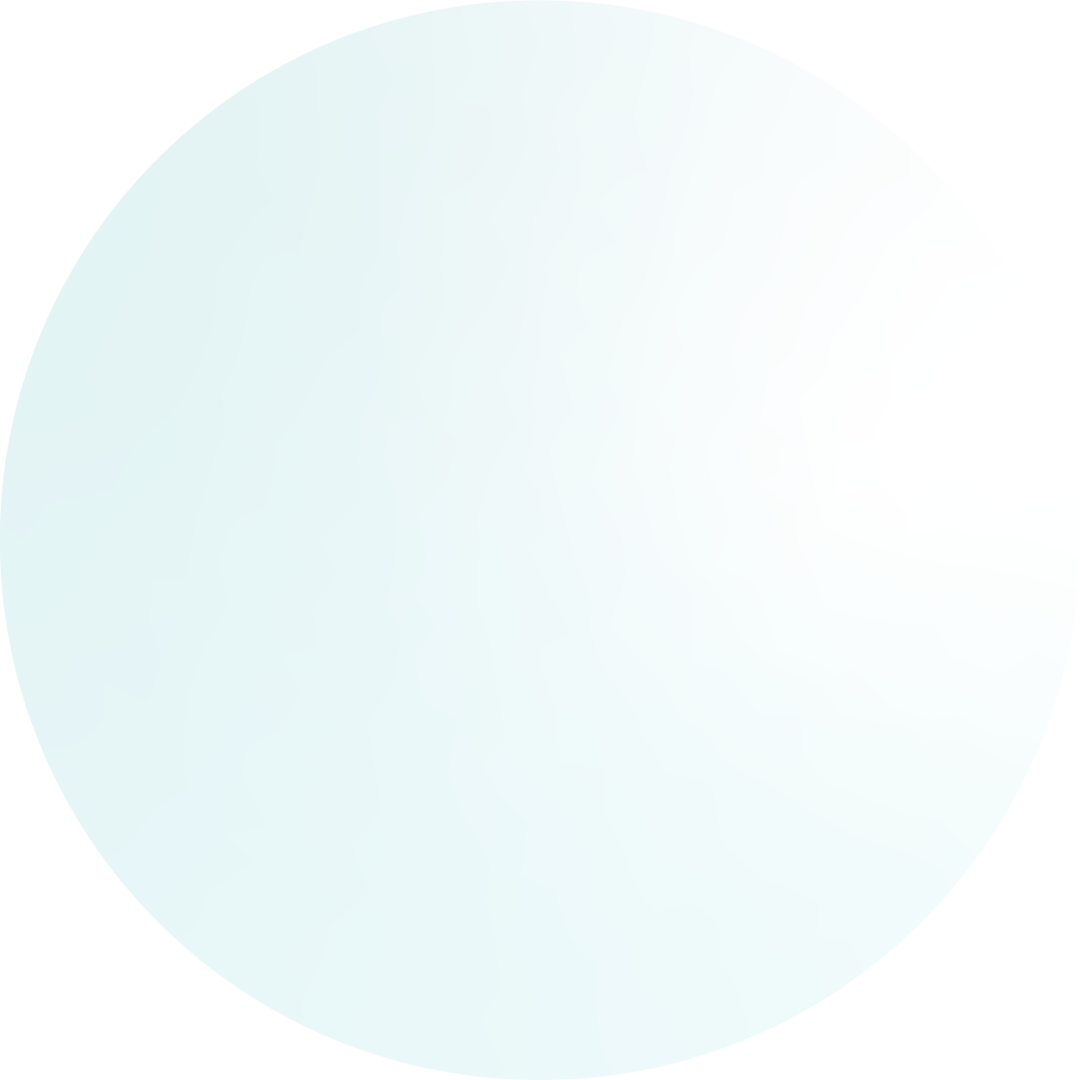
袭警案件一般具有偶发性,行为人多为初犯,犯罪手段普通,后果通常轻微,且案发后能够积极认罪悔罪、主观恶性不大,向被害人赔偿(道歉)并争取谅解的愿望强烈,办案机关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注重治罪与治理相结合,给予当事人更多出罪和从宽处罚的路径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规定的袭警罪设置有两档法定刑,分别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及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从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来看,袭警案件主要集中于一般情节,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居多,具有明显的轻罪轻刑特点。从犯罪起因看,多数袭警案件的当事人是在与他人发生交通或民事纠纷后,因对民警现场执法过程中的言行拒不配合或心生不满而一时冲动,部分为醉酒后的行为失控,呈现出明显的突发性和偶发性。从犯罪手段看,行为人通常采取拳打、脚踢、推搡、抓挠、掌掴、撕咬、抱摔等徒手打击的方式,对人身的杀伤性不强,且能及时被执法人员有效制止。从造成的后果看,多数袭警行为并未对执法人员的人身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轻微伤和轻伤所占比例较小。根据西南政法大学李永升教授对420份袭警案件判决书的梳理,其中未造成轻微伤的案件共265件,占比63%;造成轻微伤的案件有152件,占36%;造成轻伤的案件3件,仅占1%。从行为人在案发后的表现看,除个别案件中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争议外,绝大多数当事人均能认罪悔罪,试图通过赔偿、道歉,争取从宽处罚。从法院的判决情况看,李永升教授梳理的未造成轻微伤的265起案件中有76件被判处拘役,182件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7件被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在造成轻微伤的152起案件中,有128件被判处有期徒刑,24件被判处拘役;在造成轻伤的3起案件中,1件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2件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当前轻罪治理的背景下,司法机关应当落实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严肃惩处袭警犯罪的同时,积极回应群众的呼声和期待,对于符合条件的,尽可能对当事人适用法定或酌定从宽的量刑情节,其中即包括赔偿(道歉)后取得民警谅解这一能够表征行为人具有悔罪表现和社会关系得以修复的事实,从而做到罚当其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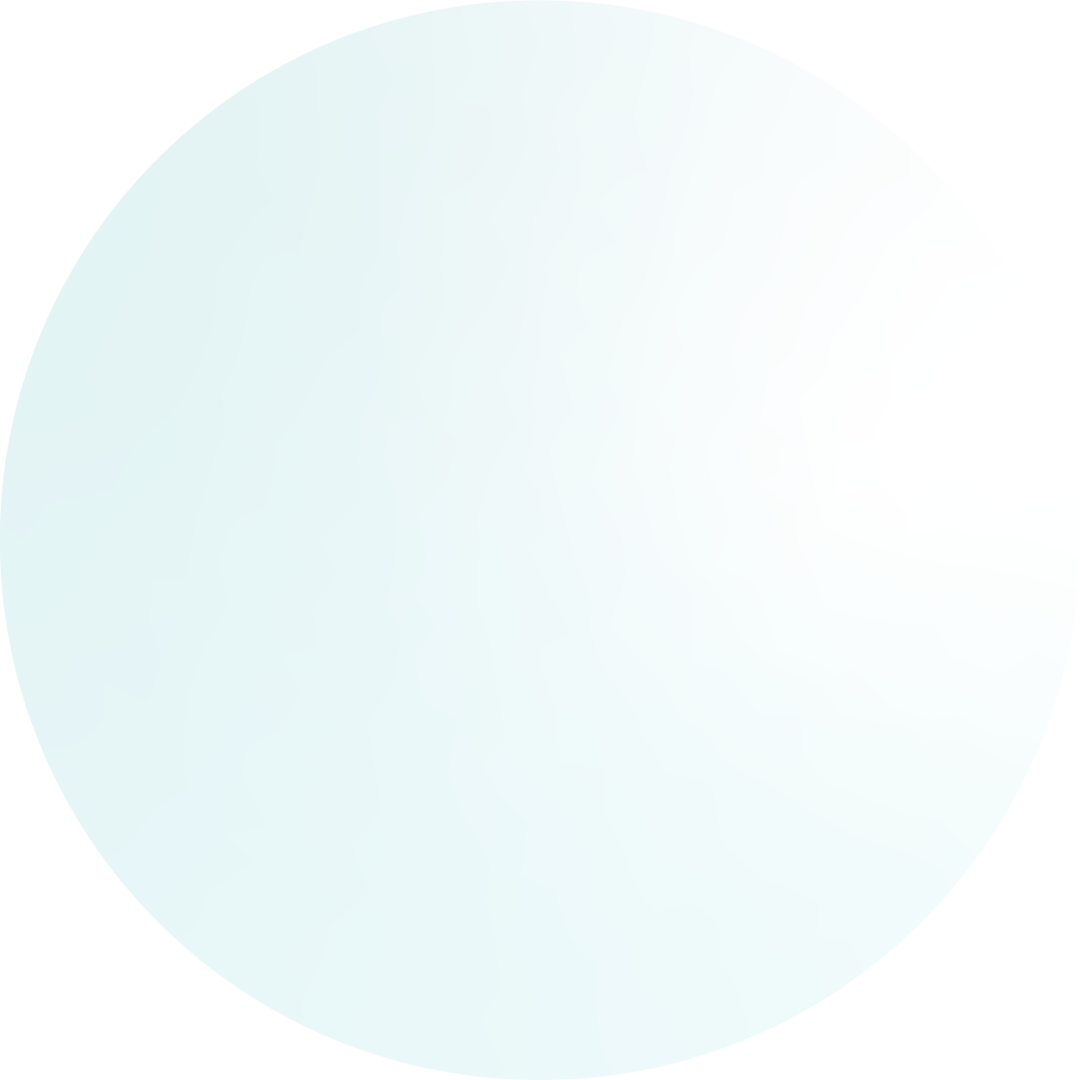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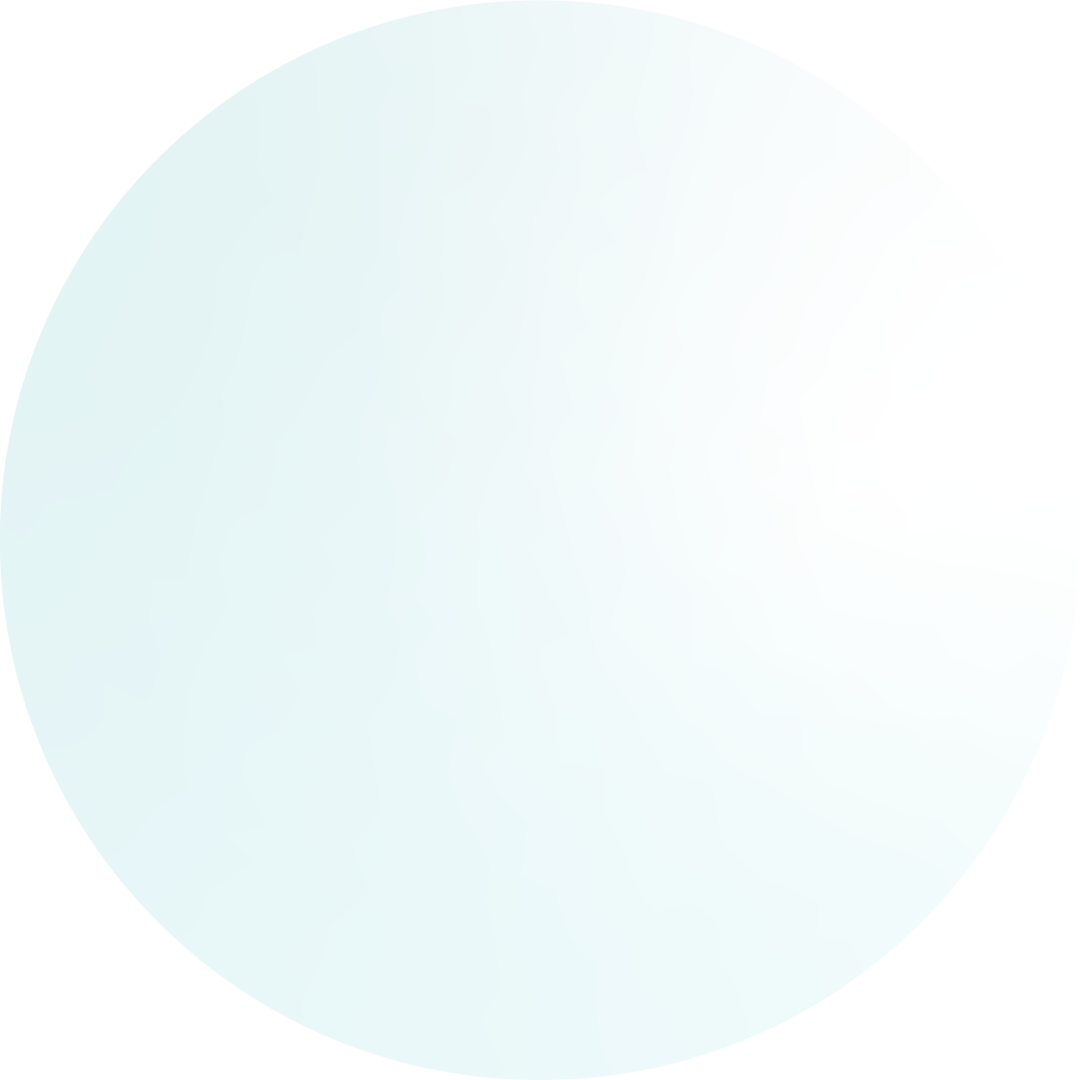
袭警罪增设之后的司法实践表明赔偿(道歉)、谅解在该类案件中具有普遍的适用空间和操作可能,在判断行为人是否认罪悔罪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已成为当事人争取从宽处罚的重要途径,得到了司法机关的鼓励及量刑上的回应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李永升教授从具体的案例中发现:“为了实现本罪量刑的轻缓化,法院也会扩张适用法定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例如,就警察的谅解而言,在袭警罪增设之前,部分法院认为其不能作为妨害公务罪的酌定量刑情节,因为妨害公务罪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公务的顺利执行,而不是警察的人身安全;但在袭警罪增设之后,法院通常都会将其作为袭警罪的酌定从宽量刑情节,甚至还有公诉机关认为能否得到警察的谅解会直接影响被告人能否适用缓刑。”有学者针对某地2020年1月至2021年9月期间妨害公务、袭警案件的赔偿和谅解情况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当地办理的妨害公务、袭警案件中有约25.1%的案件存在此类情况。这一数据也可反映出袭警案件中警察接受赔偿和出具谅解的做法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刘大伟袭警案中认定“关于刘大伟辩护人提出的刘大伟又取得受害人石某的谅解,一审判决量刑过重的的辩护意见,经查,2023年10月30日,受害人石某对刘大伟的犯罪行为予以谅解并出具了谅解书,经核实,本案三名受害者均得到刘大伟亲属的赔偿,且均对刘大伟的行为予以谅解,上诉人刘大伟真诚悔罪,一审判决量刑较重,应予改判。”除法院将赔偿谅解情节作为从宽处罚的依据外,也有检察机关以此作为不起诉的重要理由。比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对竺某某袭警案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理由为“竺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的行为,鉴于竺某某系初犯、偶犯,具有坦白情节,已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犯罪情节轻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不需要判处刑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对竺某某不起诉。”由此可见,司法机关在办理袭警案件时,多数均将受害民警个体的谅解情节作为社会关系修复的考量标准,对行为人予以了宽缓处罚,符合通常的司法经验和基本的法律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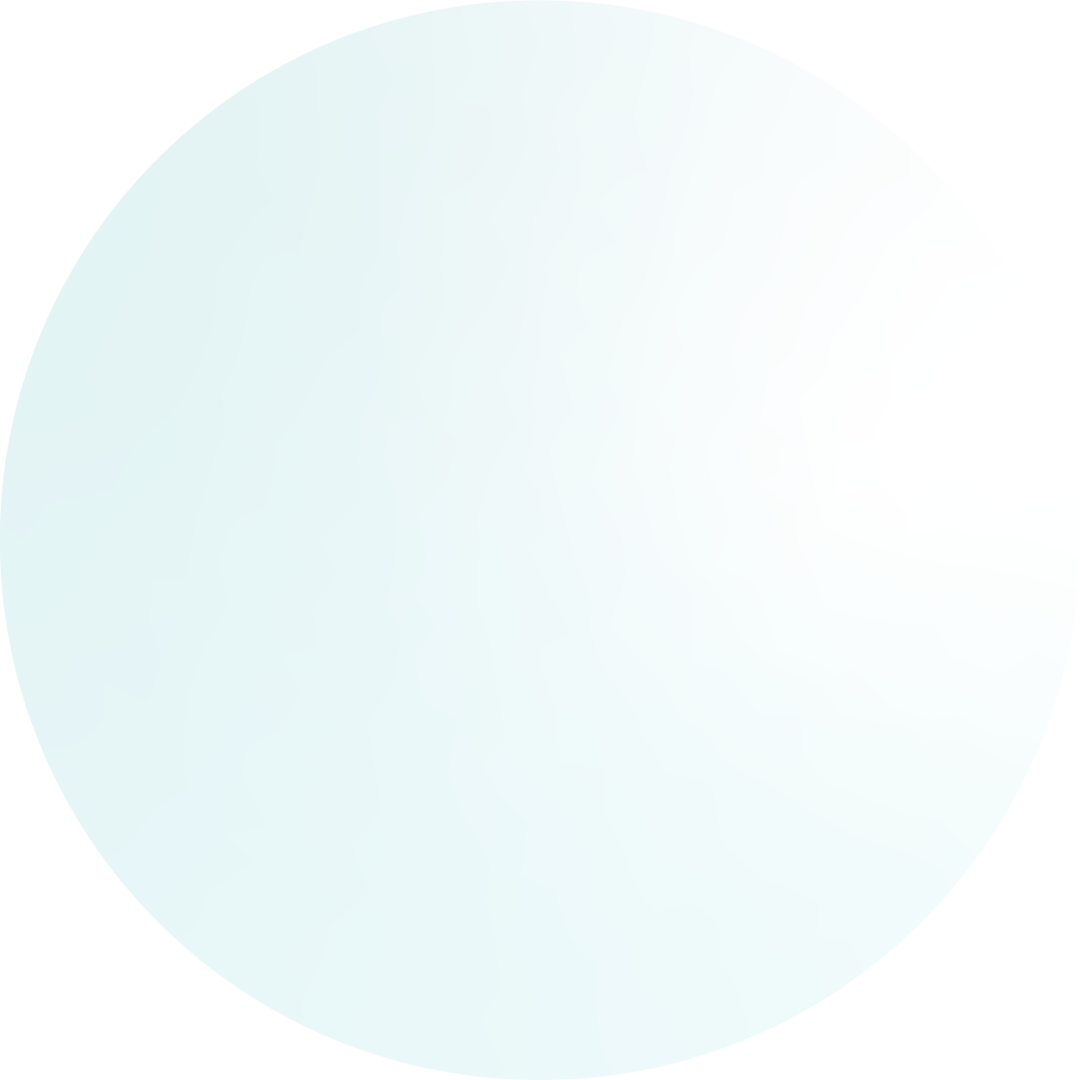
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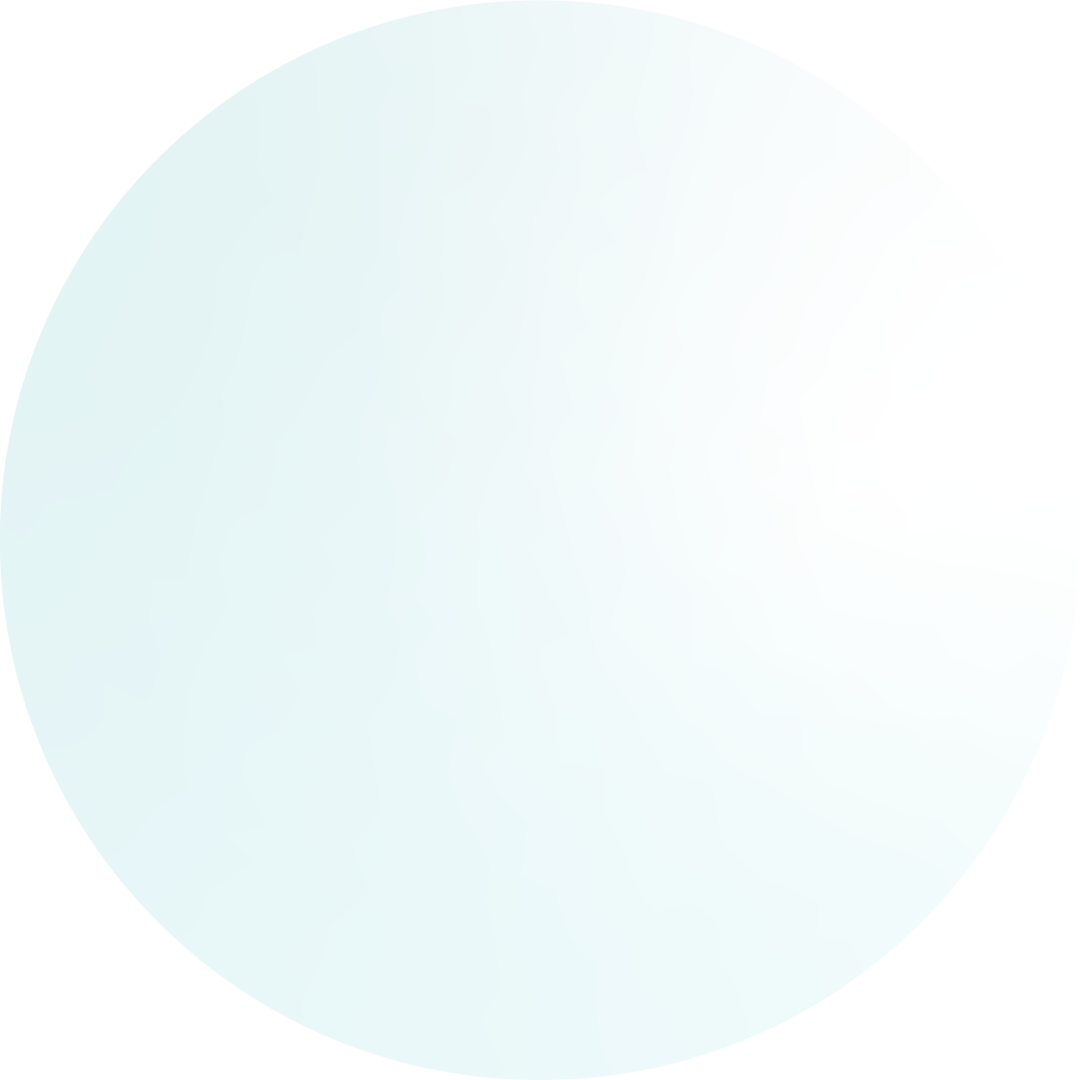
袭警罪的保护法益固然包含有超出警察个人人身安全的国家法治权威和执法秩序,但以此认为警察无权代表国家谅解行为人,只能通过刑罚才能全部修复的观点未免过于苛刻,司法机关应当尊重警察作为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给予袭警行为人合理的法律预期
关于袭警罪的保护法益,当前主要存在单一说与复合说,其中,单一说又分为“公务说”和“人身安全说”。公务说认为袭警行为侵犯的是警察的公务活动或执法权威,而非警察个人的人身权利,受害民警个人出具的谅解不能作为对行为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人身安全说强调设置袭警罪的目的是保护警察个人的人身安全,相应地警察个人可以处分自身的权利,比如接受赔偿同意谅解。复合说是公务说和人身安全说的结合,既包括执法秩序和权威,也包括警察的人身安全。在此观点下,警察个人的谅解能否作为对行为人从宽处罚的依据便产生了争议。正如1589号案例分析中所言“民警个人的谅解仅代表对民警个人法益在某种程度上的修复,并不意味着被破坏的公安机关执法秩序和权威得到修复。”欲论证该问题,需要厘清国家法益与个人法益之间的关系。对此,张明楷教授认为“国家法益与社会法益都必须能够还原为个人法益时,才可能是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在此意义上说,对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侵犯最终都是对个人法益的侵犯。”易言之,集体法益是个体法益的集合,抽象无形的集体法益只能通过行为人对具体有形的个体法益的侵犯方可遭到破坏。据此,袭警犯罪破坏的法治权威和执法秩序只能通过行为人对民警个体的人身侵害所实现,直观体现为民警人身的损伤和公务行为的中断。可见,袭警罪保护的秩序法益和个人法益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先后关系、表里关系,没有对民警人身的暴力袭击,自然不产生执法权威的损害;没有民警个人权益的修复,执法的权威和秩序当然也无从重塑。民警个人当然无权代表国家原谅袭警行为人,但是民警个人的谅解、警民关系的修复恰是执法权威和秩序弥合的前提和基础。2019年《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被袭民警的被害人地位,其自行处分受损人身权利具有法律依据,对行为人出具的谅解不仅是个人法益的修复,而且是执法权威重新树立的起点。文章认为“受害民警接受犯罪分子的赔礼道歉并予以谅解的行为是否会间接影响人民警察的执法威严,进而给社会安全和秩序带来不良影响,值得反思”的观点仅为观念上的偏见,并无法律上的障碍,在赔偿数额和方式上,完全可通过民警所在单位的监督管理予以制约。如果一味坚守国家法益无法通过被害个体进行修复的观点,明显超出了普通民众的法律认知和经验直觉,不仅对大多情节轻微的袭警行为人过于苛刻,而且限缩了警民关系的恢复路径,有可能产生新的对立和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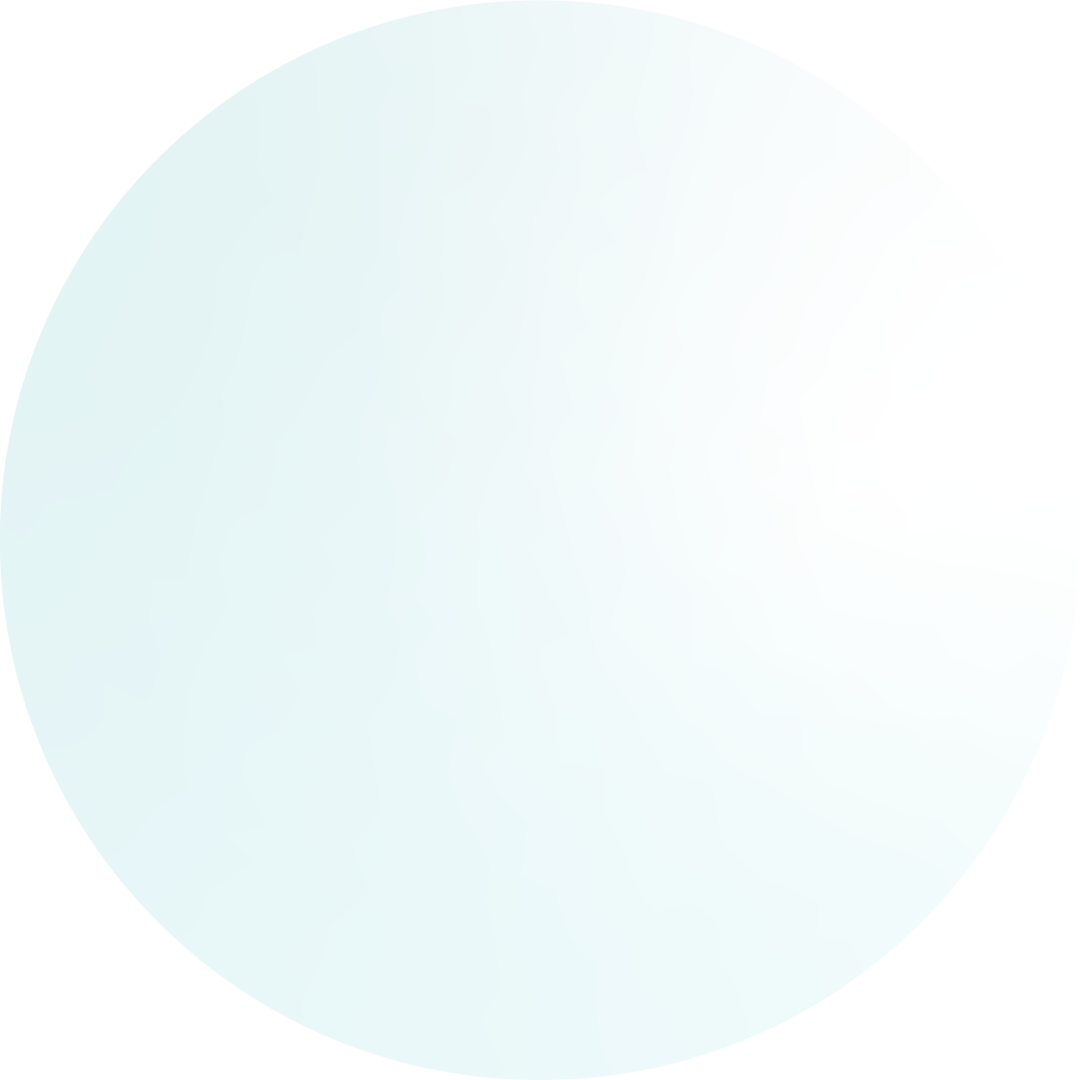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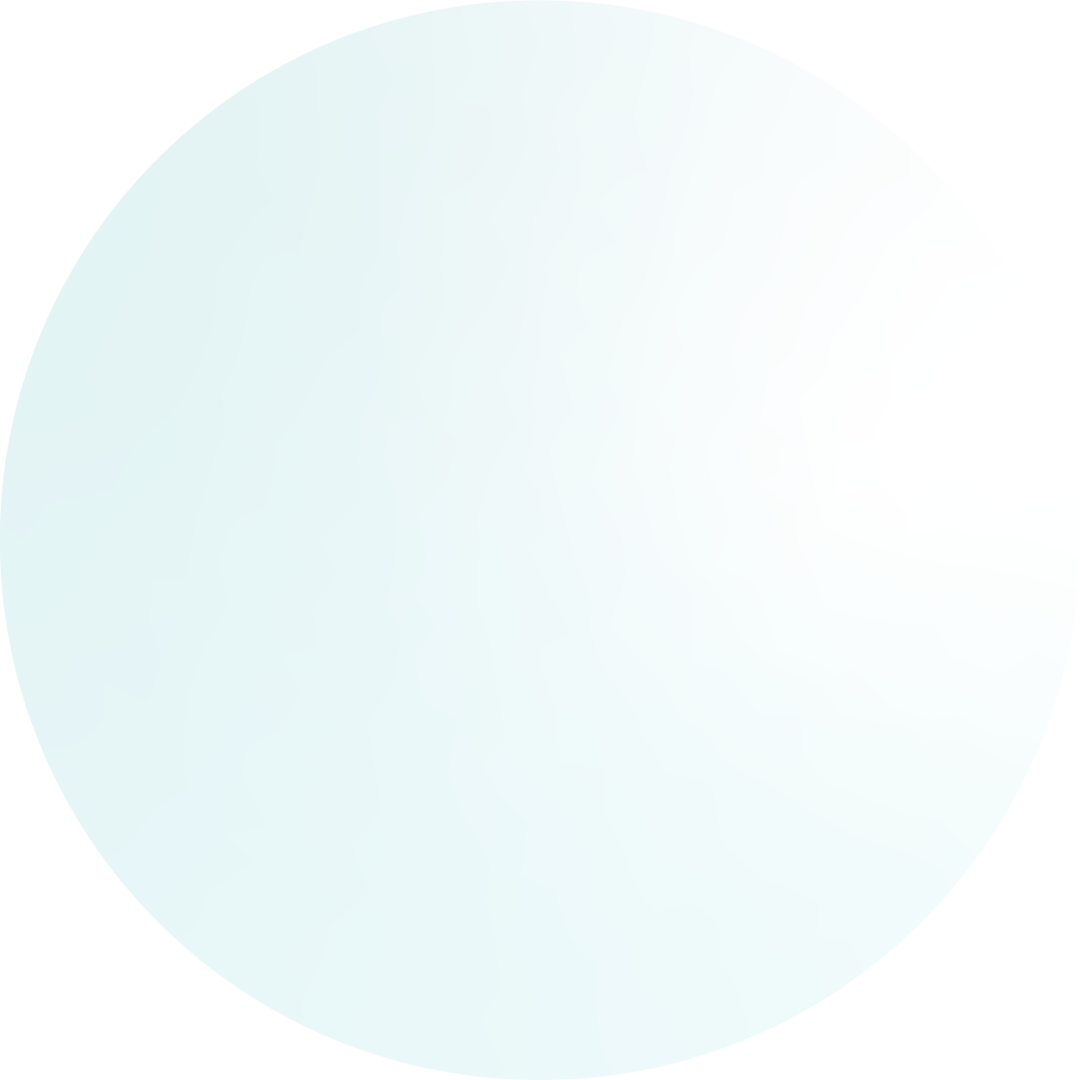
赔偿谅解作为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在袭警案件中具有表征行为人积极认罪悔罪、预防必要性减小的重要意义,应当与其他从轻情节分别适用、重复评价,仅将其作为“是否真诚悔罪的依据”会造成行为人量刑利益的减损,背离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两高”《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将赔偿和谅解作为常见的从宽量刑情节之一,区分赔偿和谅解的具体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40%以下,对被告人是一项重要的量刑优惠。同时在量刑情节的适用上强调“量刑时应当充分考虑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根据案件的全部犯罪事实以及量刑情节的不同情形……对犯罪情节较轻的犯罪,应当充分体现从宽。”在此指导下,各高院、省检院制定了量刑实施细则,进一步对赔偿和谅解情节的适用进行了细化,部分地区还对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规定了不得超过10%的基准刑减量。综合上述规定可见,赔偿和谅解在刑罚裁量中呈现出轻微犯罪一般适用、严重犯罪有限适用的基本特征。《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规定“对于构成犯罪,但具有初犯、偶犯、给予民事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的,在酌情从宽时,应当从严把握从宽幅度。”这一规定明确了在袭警案件中,赔偿和谅解依然是重要的从宽情节,对于总体轻微的行为可以适用,但需限制从宽的幅度。因此,文章认为“赔礼道歉、获得被害民警谅解只能视为犯罪人为悔罪而作出的努力及诚意,仅是判断其是否真诚悔罪的依据”忽视了赔偿和谅解情节的独立地位,未能发挥出该情节在从宽量刑中的“增值”功能,可能导致量刑偏重、罚过其罪的问题。
袭警犯罪破坏社会管理秩序,损害国家法律尊严,固然应当严惩,但是,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亦应当贯彻落实。对于大多数的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大,行为暴力程度较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袭警行为人,应当鼓励其通过赔偿或道歉获得民警的谅解,从而给予宽缓的处理;对于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民警人身安全的袭警行为,则应当限制该情节的认定和适用,确保裁判结果合法、合理、合情。
律师简介

李洋 律师
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毕业于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学系,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硕士,曾供职于军事检察院公诉处、刑事诉讼监督处,获得全军检察机关“十佳公诉人”称号。执业以来,先后办理山西某信用社李某受贿、违法发放贷款案、北京某大型民营企业董事长陈某行贿案、北京市梁某受贿案等多起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案件。
制作:韩 雪
审核:冯发海

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02年。经过20余年发展,现已成为一家专业齐全、服务优质、极具口碑的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业务涵盖刑事辩护、民商事诉讼与仲裁、银行保险、股权投资、资本市场、企业改制、政府法律顾问、知识产权、建筑与房地产、破产清算、国际贸易与投资、公益法律援助领域等各个领域。2022年6月,东卫组织形式变更为特殊普通合伙。
东卫北京总部现位于首都核心区,目前在全国拥有1200余名人员,其中近百名为博士后、博士律师,十多名法学专家教授为兼职律师,并聘请全国知名学府法学专家、多名实务专家担任东卫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能够为客户提供权威、及时、前沿、有效的解决方案。
东卫以“学院派”为特色,成立有多个法律智库平台,设有齐全的专业机构,举办多次高端论坛,专业能力领先同行。同时,东卫还与多个海外法律服务机构保持长期合作关系,能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多样化、国际化的法律服务与支持。
Main Honor
北京市律师行业先进律师事务所党组织
律所卓越品牌影响力
中国律所品牌价值100强
北京商务服务业创新品牌100强
全国商联法律维权服务中心律师团成员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企业合规评价建设单位
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法律定点服务单位
全国律师行业优秀共产党员
北京榜样·十大律师楷模
北京市优秀律师
三八红旗奖章
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
“今日头条”年度最佳合作律所
中国优秀知识产权律师榜TOP50
北京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优秀团队
中国房地产业营销协会副会长单位
《中国版权》理事会理事单位
助力金融风险防范机构
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优秀律师
北京市百名优秀刑辩律师
ALB十五佳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东卫民商研究院
东卫刑事研究院
全国刑事业务研究中心
全国金融业务研究中心
全国刑民交叉业务研究中心
全国涉外法律业务研究中心
全国知识产权业务研究中心
全国合规与风控业务研究中心
全国环境与资源业务研究中心
全国公司与并购重组业务研究中心
全国证券与投资基金业务研究中心
全国破产重整与清算业务研究中心
全国行政与政府顾问业务研究中心
全国劳动与人力资源业务研究中心
全国互联网与数字经济业务研究中心
全国建设工程与不动产业务研究中心
全国诉讼/仲裁/调解多元争议解决中心
全国婚姻家事与家族财富管理业务研究中心
全国特殊资产暨重大执行案件业务研究中心
Branches

Contact us
法律咨询:dongweiad@dongweilawyer.com
人才引进:hr@dongweilawyer.com
媒体合作:dongweifirm@dongweilawyer.com
联系电话:010-65542826/27
总部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D座三、五、六层
Follow us
官方网站:https://dongweilawyer.com
微信公众号:东卫律师事务所
微信视频号:东卫律师事务所

点击关注
东卫律所
Statement
本公众号所载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或仅为提供法律信息,不应视为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任何依照所载内容实施行为(包括作为或不作为)所产生的后果,本所及作者本人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原创文章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获取授权。
Map
